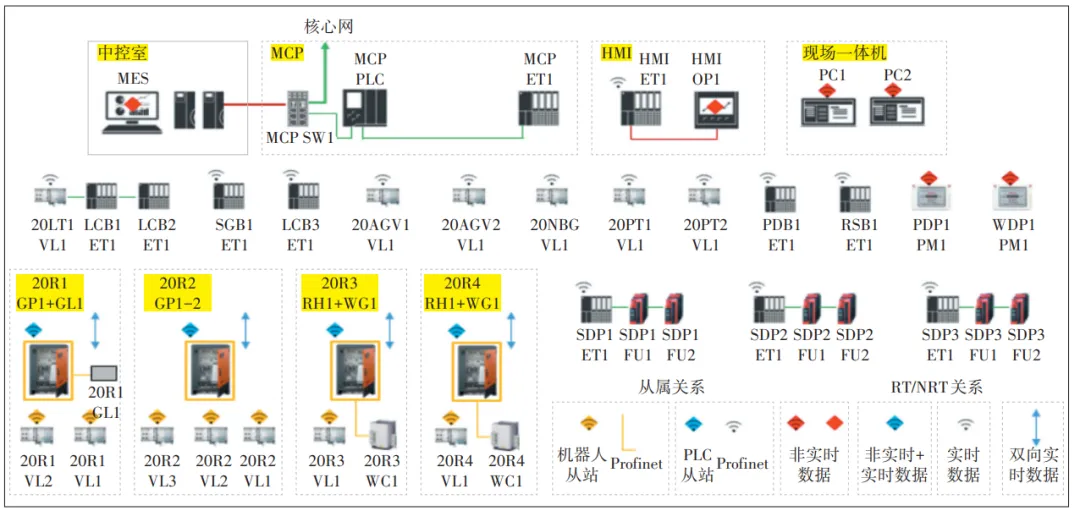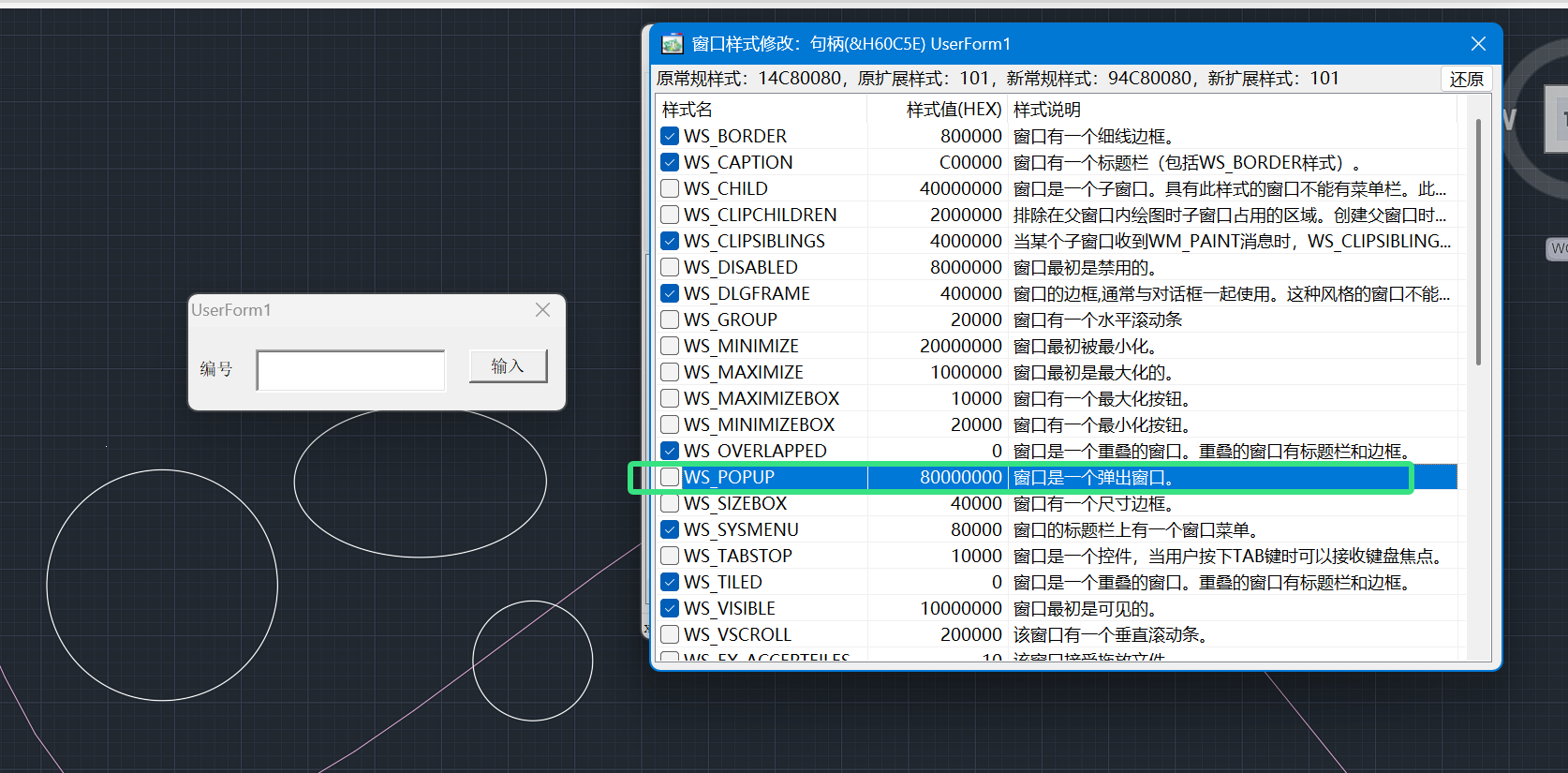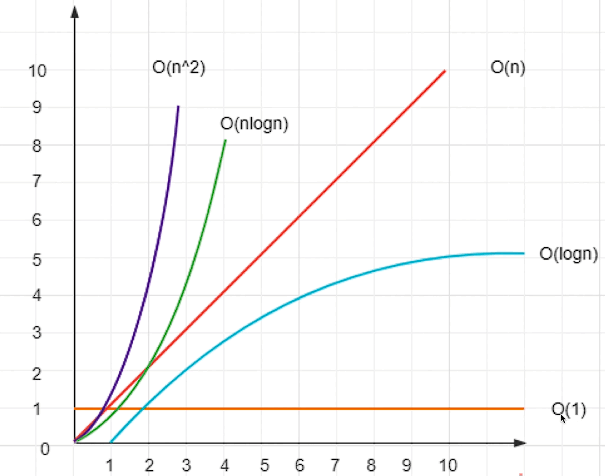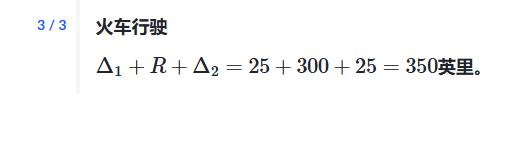成都的冬天,是带着厚重眼镜的,挂着风干鼻涕的历史系学生,可能强于一具新鲜的尸体。
痛苦是我的血,我切开静脉,看她们提着长裙从容走出我身外,向阳台上的两只刚刚飞走的麻雀微笑执意。致敬!我永远的朋友,她们竟慷慨地愿意分享我的脏话。致敬!我本以为她们人数不多,但现在看来她们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
是你,不以进化为目的的进化,让本该魅力四射的我不得不言辞朴素,不得不表情严肃,可恶的,你打断了我本该珍藏的初吻,你撕烂我本来荣耀而完美的翅膀,只退还给我手淫的权利和不知是否还安全的残破降落伞;
是你,最高明的驯化,最壮观的马戏,赐予我长跑的毅力和无数的纸笔,吸允尸体们的营养啊,亲爱的,你给我绽开的微笑的樱花,给我漫天的红的绿的黄的烟火和对它们的向往,即使是梦境,我的余生的唯一意义也将会是撰写这梦的回忆录。
神说,没有恨。我说,没有恨,异口同声。真的是“异口”吗?应该是。我不是弥赛亚。也未必。神也不是弥赛亚。
我说,没有恨,于是所有恨的假象都消散。
我从此只听得见礼赞。
看!她们走来了!她们依旧从容地提着长裙,带着微笑,不过我看得更为清晰了,破旧的暗红的地毯翻涌,变成滚烫的鲜红,还有那往后的素白雪地,也印下她们青春的足尖。她们走进峡谷,而后峡谷闭合,她们在里面说:跑起来!跳起来!舞起来!
听风声摇乱,但婆娑的不是风;吹动烛火翩翩,但翩翩的不只有火。深夜律动过后,我将与明早的太阳一起,加冕成为这片废土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