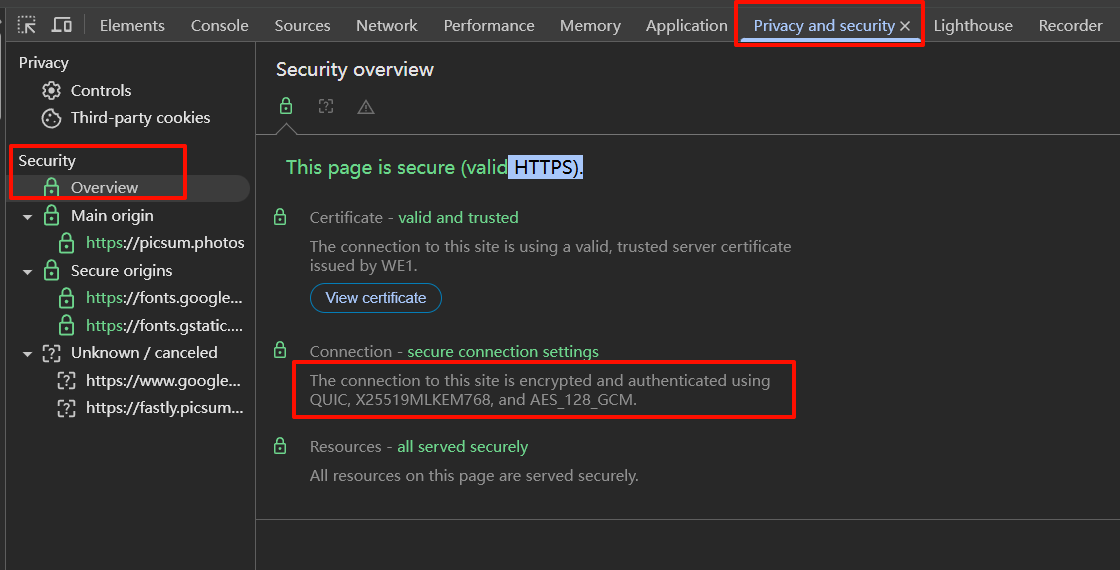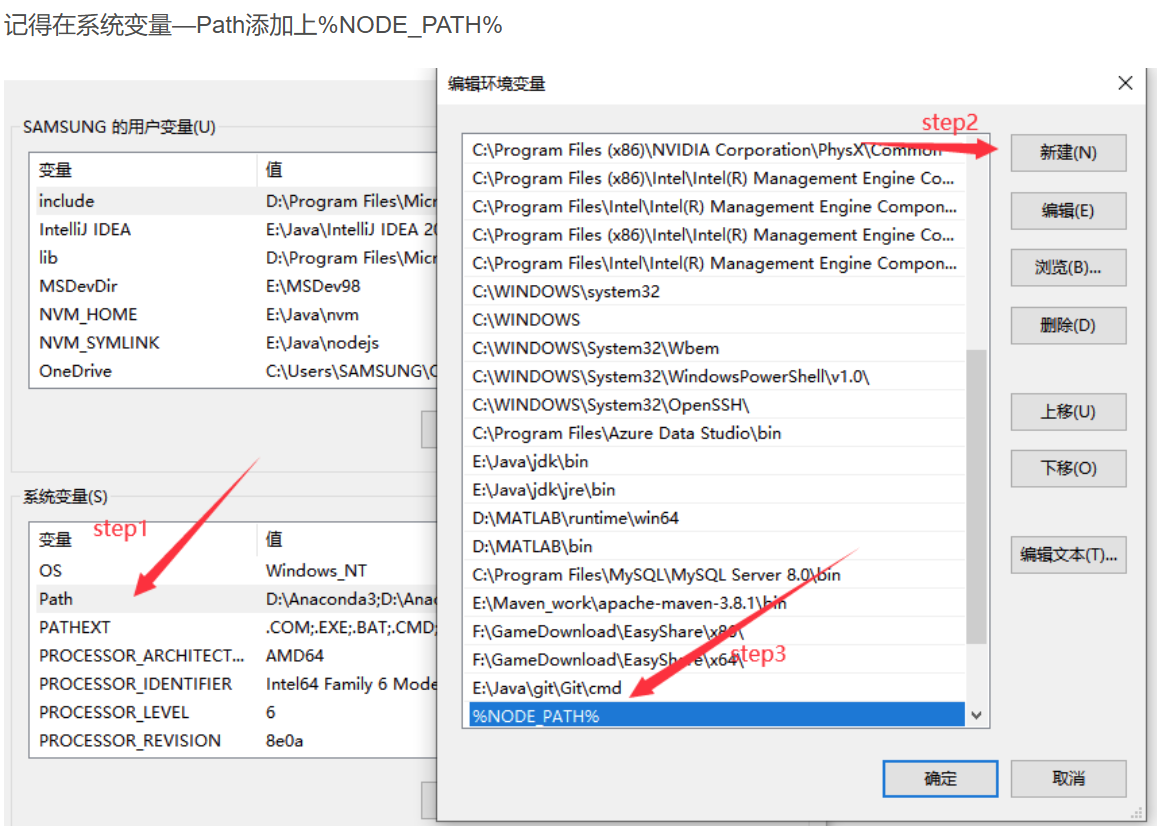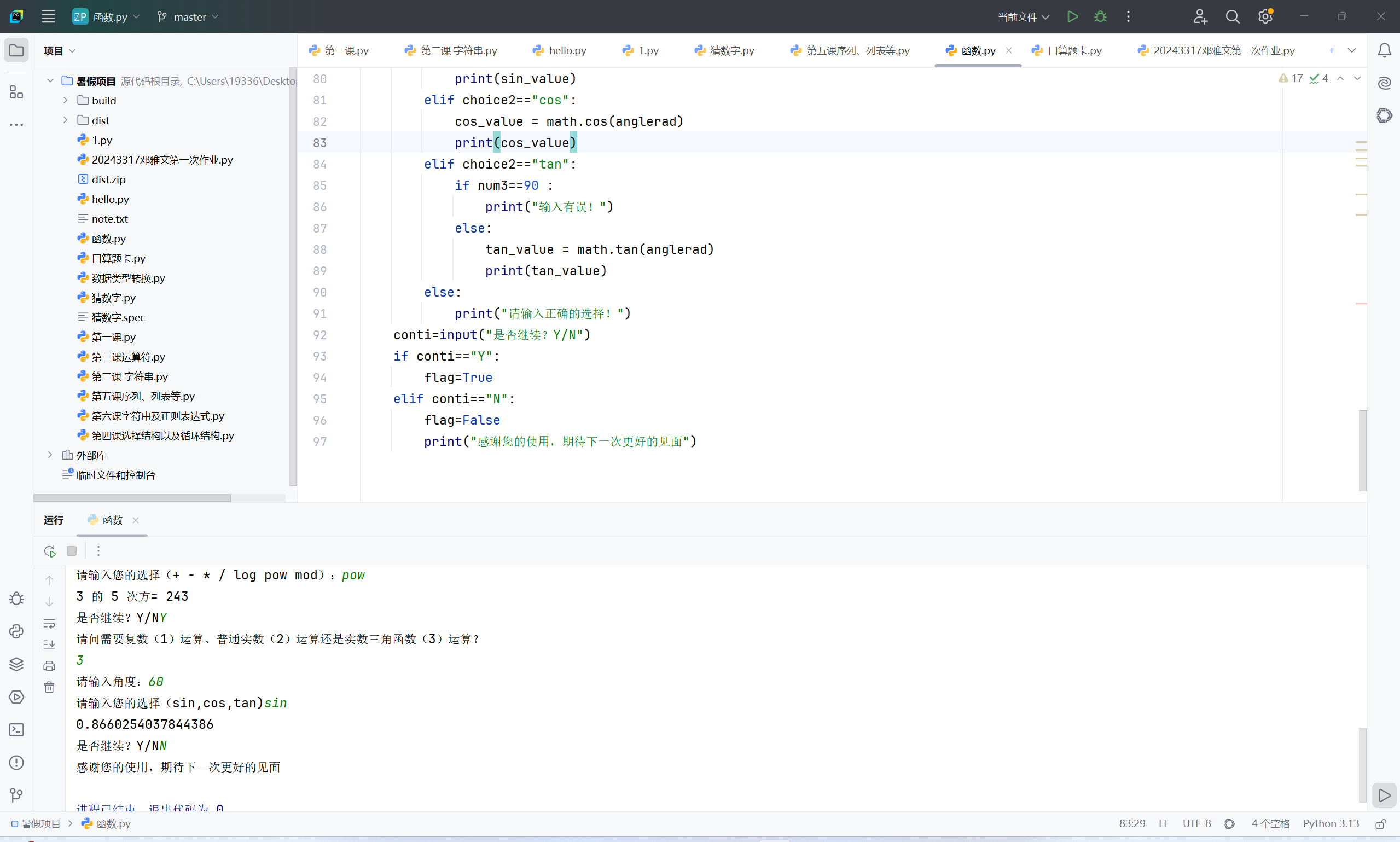诺米·科托博士(Normi Coto, PhD)

配图来自 Unsplash 的 Element5 Digital
3 月 15 日星期六,我参加了一场名为“人文学科中的 AI”的职业发展工作坊。会场人满为患,坐满了来自弗吉尼亚州中学和高中的英语和历史老师。来自弗吉尼亚大学和朗伍德大学的教授主持了这次工作坊,主题聚焦在几个方面:教我们 AI 是如何运作的(更像我们的大脑而不是计算机)、教师自己如何使用 AI(比如差异化教学设计),以及我们为什么必须教学生 AI(它不会消失,而且已经写进我们州的教学标准里了)。这些教授来自不同的系,比如天文学、英语、教育。他们的演讲内容丰富、生动有趣,极具吸引力。我学到了很多,吃得也很好,而且这场工作坊是免费的——如果你不算上投入的时间和汽油的话(来回开车 6 个小时)。尽管这些讲者都很努力,我还是感到有些失望。我离开时,心里有许多问题得不到答案,对写作教学的未来感到一片灰暗。
你可能看不到,但你一定能感受到:房间里有一道看不见的线,一边是讲者,一边是老师。换句话说,大学教育者和 K-12(幼儿园到高三)教育者之间的态度和世界观截然不同。
当然啦,我们这些老师很高兴能学到一些 AI 小技巧来快速设计出适合不同学生的教学内容。我们也喜欢 AI 能帮助我们更快地给写作作业反馈,希望能省下一些周末改作业的宝贵时间。
但每次休息或午餐时,桌上的话题总会回到一个老问题:“你们学校怎么应对作弊学生?”我听到的一些回答有这些:
“我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加入了个人叙述、采访和调查,这样学生就不能全靠 AI,或者至少不能全部靠 AI。”
“我的学生必须手写所有内容。”
“我们让学生签署合约,承诺不会用 AI 来写整篇论文。”
“我让学生先手写一篇诊断性初稿,以后交的每篇文章我都拿来跟这篇比。”
“学生的第一稿要用纸写。我会复印一份,然后以后他们交打字稿时,我就拿来对比。”
“我完全线上授课,不能用纸。如果 AI 检测器高亮了哪怕五个词,我就打电话给家长。如果家长说他们孩子没用 AI,那我也没办法。”
尽管大家桌上聊得都是这些话题,那天的主旋律却是:我们必须教学生 AI,否则他们将来进不了社会!真的吗?难道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要是我没教比利怎么在 ChatGPT 里写出一个有效的提示词,他将来就找不到工作了?将来会不会有个成人版的比利,一本正经地责备我:“你当年竟然让我手写《科学怪人》里主题分析的文学评论,而不是教我怎么分辨 AI 吐出来的内容是不是假新闻。”
等等!“我必须教我的学生如何‘合乎伦理地使用 AI’。”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工作坊上举起了手,说了以下这些话:我教学生用 APA 格式写论文,所以我们经常深入讨论“抄袭”这个问题。他们能看到一篇论文后面的研究者名字,明白不应该窃取别人的成果。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写的。但 AI 不一样。我的学生把 AI 当成一个工具,不是一个人。尽管如此,我还是会跟他们解释,为什么用 AI 来写论文是不道德的。就像总会有学生抄袭(尽管通常不是故意的),也总会有学生用 AI。但用 AI 来写整篇文章,为的是省得自己动脑动手,那就是明显的“故意”。问题在哪儿?我没有一个“研究者”可以指着他论文说:“你看,比利,你就是照搬了这个科学家的原话。来,这是原文。你重写这一段。”现在我要先把 AI 写的论文放进 AI 检测器里跑一遍,这检测结果有时候对,有时候又不准。但我心里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比利作弊了。比利当然一口否认用过 AI。然后我就只好这样反馈他:“哇,比利,这篇文章写得太棒了。你这一个月连一句完整的句子都没写出来,可这一晚上就写出了一篇结构完整、段落清晰的论文,真是太神奇了。我希望明天在课堂上还能看到你这样的写作水平。”……一片寂静。写出这种反馈的时候,我总是会变得刻薄。可一个老师刻薄,真不好看。
大学教授和 K-12 老师之间的那道“分界线”,在有人提到“考试”和“教学标准”的时候,就更明显了。“我的教学标准里,有一项是要学生掌握主谓一致,还有主动语态胜于被动语态,”后排一位老师对台上的教授说,“那我怎么知道他们到底掌握了没有?他们的草稿都被 Grammarly 改过了。”……一片寂静。另一位老师讲了她面对的困境:她不仅要教育学生,还得教育家长。那些白领家长自己可能也在工作中用 AI,他们理解道德层面的问题,但也知道 Grammarly 这种程序对他们多有帮助,于是就觉得没必要禁止学生使用。蓝领家长对 AI 比较陌生,不知道孩子用 AI 有什么问题。他们的孩子只是在“用谷歌”而已。
我带着满满一车的教学设计点子和改作业的好工具离开了这场工作坊,却没有得到一个“面对学生整篇用 AI 写作”的解决方案。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大学教授和 K-12 老师目标上的差异,尽管我们都是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 K-12 的学生缺乏内在动力。而大学生因为自己花钱上课,更愿意投入。大学教授在备课上也更自由,不会像我们这样有考试和标准的压力。因此,年纪小的学生在签了合约、学了道德之后,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使用 AI。我们也必须承认,K-12 的老师被考试和州标准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 AI 又成了我们要应对的另一个障碍。
老师们知道 AI 很重要。老师们知道 AI 是挡不住的趋势。但不是所有老师都觉得 AI 应该出现在 K-12 教育中。
这次工作坊上,所有老师唯一达成一致的共识是:我们希望所有阶段的学生都能独立思考,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AI 的“评估”成了突破口。换句话说,我们被教导:要在课堂上直接拉出 AI,让学生来评估它的输出内容。老师们(还有图书馆管理员)本来就花了很多时间教学生如何评估信息来源,所以,评估 AI 的产出,也算是顺理成章的延伸。我们扛得住。但是——还是那句话——我可以明确告诉比利:“不能拿维基百科当资料来源,回去重找资料。”但我却无法在比利用了 AI 的时候,给出同样明确的回应。
上周,我有个学生用了 AI。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平时连一封通顺的邮件都写不出来,结果却交上来一篇分析他选择的视觉作品里“视觉隐喻”的论文。我让他看,两个 AI 检测器都标红了他的文章,可他还是死不承认。我问他“什么是视觉隐喻”,他答不上来,却说自己是和家教一起写的。我让他手写重写一遍,他不再回应我,最后写了一篇三年级水平的文章,还是坚决否认用过 AI。我们在这来回拉扯上浪费的精力,精神的、情绪的、身体的,原本都可以避免——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强制使用笔和纸,或者所有写作都必须用不联网的文字处理器来完成,并且只能在课堂内写作。
尽管这次的讲者们对 AI 都是正面态度,但高等教育本身仍然充满了关于“怎么处理 AI”的不确定性。不是所有教授都觉得有必要教 AI,就像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责任教学生怎么看 YouTube 一样。有人说,现在这个时代是“狂野西部:AI 版”。而我,更愿意等风沙落定之后再说。
一如既往,奔跑,勇敢前行!